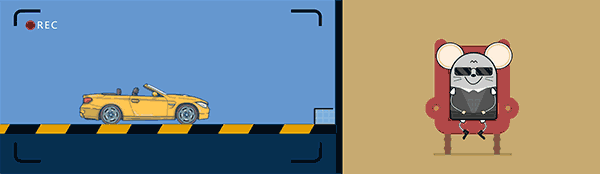那是一个深秋的日子,一场冰冷的秋雨洒落,我穿越遥远的新疆阿羌,留下了一段被雨水淋湿的回忆。
阿羌乡,位于且末县西一百二十里,阿尔金山北麓,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且末,有着太多美丽又神秘的传说。这里是楼兰女王曾经的属地,罗布泊、太阳墓、小河遗址,似乎都与且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然而,对于我——一个离家几千里,奔波劳碌的卡车司机来说,我更关心的是如何越过那些巍峨险峻的大坂,和反复无常的暴虐天气。
我驾车行驶在国道上,思绪飘飞,思考着即将面临的难题。国道三一五平坦笔直,黑色的柏油路面似一条绸缎伸向远方,我的陕汽德龙3000喘着粗气,越过戈壁,吼叫着冲向海拔四五千米的阿尔金。灰黄的骆驼刺从倒车镜里飞快地逝去,公路两侧时而有枣园时而有棉田,勤劳朴实的人们意志如胡杨般坚定,他们战风沙斗干旱,在这千里戈壁滩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
离开县城四十公里后,国道与我分道扬镳,315的路还很长,这里距喀什还有将近九百公里吧,无人区、荒漠、渴死的胡杨,也许还有三千年的干尸都在未知的旅途上。这是一场时间与生命赌博的路线,几年前,在塔什拉玛干交通卡点,沙漠公路无人区的起点,每逢傍晚至次日凌晨是不允许车辆驶入的。如果确有急事必然进入,警察会为你登记备案,如果到了预定时间还没有在终点出现,那么就会有救援队去无人区里寻找。
我思索着,或许我也好不到哪儿,315上虽说也没有补给,但是偶尔经过车子的还能带来生命活动的痕迹,还能给人心里带来小小的慰藉。而我呢,只有默默地、孤独地、忐忑不安而又有心怀恐惧的走进那白雪茫茫的阿尔金山的怀抱里。
轰鸣的车子越过无数个涵洞、漫水桥以及坑坑洼洼的土路,终于驶上了大桥,下了桥几百米就是阿羌乡,它或许是我多少年来见过的最小的乡镇,只有一条街道,大概有一百米长?也许还不到吧,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打量一番,缓慢行驶的大车已经出镇了,拐上了崎岖不平的便道。
路牌显示:距离铁里木金矿还有一百八十公里。一百八十公里,如果在高速上行驶可能用不了两三个小时,可是在这里,在阿尔金山,来回却得整整一天,沿途要翻越两座五千多米常年飘雪的大坂,还要跋涉数不清的大河。那盘旋在云遮雾绕上的山道更是惊险万分,崎岖不平的道路虽然没有怒江七十二拐的弯道多,悬崖峭壁的高度绝对是惊人的,从上向下俯瞰,河流成了一根鞋带子,蜿蜒曲折流向阿尔金山腹地。最让人发愁的是那如同天梯般的上坡,车子虽然桥、轴都上了差速锁,但还是打滑上不去,飞速转动的车轮刨出的石子土块,打在泥瓦上啪啪作响,最后没得办法只好升起了车厢,才勉强爬了上去。
前途叵测啊!想起时而狂风、时而暴雪的天气;想起挥之即来、倏尔就去的冰雹,想起传说中有如幽灵般游弋在沙河里的淘金船,想起神出鬼没的棕熊和野狼,心中越发忐忑不安了。唉,我神圣阿尔金山,你真的是我逃避不的噩梦啊,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还是走吧,进山!
(二)
离开阿羌乡仅仅十公里左右,车子就出现了故障。经过一个急转弯时,一股浓烈的柴油味弥漫在驾驶室里,这一段容易发生塌方和泥石流,淤泥夹杂着石块涌到了狭窄的路上,右侧是洪水泛滥后冲出的深沟,哪里还敢片刻停留,我小心翼翼的操纵着汽车压着泥浆从沟壑边驶过,天色已晚,从倒车镜里看见胎面上粘满了灰色的泥水,车子左右打滑,差点掉进深沟里。
缓缓地靠边,在一段稍微平坦的路上停下车,熄了火,从气味散发的位置分析应该是柴滤或油管的故障。顾不得满地的泥水,一头钻到车下,在头灯的照射下,车架缝隙里,一个柴滤正滴滴答答的淌着油,还好故障位置靠下,驾驶室也不用打,我从钢板的缝隙伸进链形扳手想要拧掉滤芯,可是,也不知给我保养车子的兄弟固定时用了多大的劲,怎么也拧不下来。无奈只好用小撬杠穿进去,来了个破坏性的拆卸。
换好滤芯,天已经黑透了,在冰冷的滤水下洗洗手,就上车赶路。新疆的白天长,太阳落山的比较晚,估计时间应该快二十三点多了。我收拾好工具,发动车,雪亮的大灯照射着沙石路面,崎岖不平的公路或凹或凸,摇晃着慢行,不知尽头在何方?
遥望漆黑的夜幕,前方隐约有亮光,我知道距离金矿加工厂不远了。那里是这段漫长旅途中唯一的一座厂子,从阿尔金山深处运出的金矿,一部分送到了且末县城一部分运到这里进行粗加工,最后由长途半挂车拉到格尔木或者宝丰提炼。
从西部大开发的牌坊下经过,一直下坡再下坡,像崖壁一般垂直的路,坡度特别陡,陡得一头就栽进了河里。这是我进山经过的第一条大河,水很深很急,水泥铺就的路面埋在水下,根本看不到,只能估摸个大概的宽度,就加大油门冲了过去,车子两侧溅起的水花,好像一艘快艇在海面上冲浪。这里其实就是一座隐形的漫水桥,没有从这走过的人,无论如何也不敢下水的!
过了河,就是上坡。凭着多年在青疆藏跑车的经历,我知道像这种V字形的峡谷路,马上就要上大坡了。车灯直直的,雪亮雪亮的灯光像是要打到天上,路好像是垂直的架在房子上的梯子,汽车打着滑向上冲着,刚刚被水浸湿的轮胎一会儿就打着旋的干了!轮胎下的石子被一块块刨了出来,又如利箭一样甩到车后!
爬完了这段陡坡,又忽高忽低的驶过几段U字形的孱坡,终于来到了吐尔斯曼村!村子静悄悄的,村子所有的建筑就是几座低矮的土胚房,默默的散落在公路两侧。羊圈更是简陋,连围墙也没有,只用些木棍树枝扎了圈圈就算是篱笆了吧……
村子中央有一座联通信号塔,它是这个闭塞坏境里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建筑了。正在此时常德小胡的电话打来了,他是先我一天出发拉矿的车子。小胡是湖南人,个子不高,人却很机灵,我们在若羌修库格铁路时认识的。
记得那是一个下午,天气本来是标准的西部风格--蓝天白云。可是装上戈壁料以后,不知道哪位弟兄触犯了老天爷,转瞬之间天气骤变。蓝天被罩上灰黄的面纱,空旷无垠的戈壁没有一点点风,一粒粒沙子紧张的挤靠在一起。骆驼刺不安的探着身子,干枯的枝叶组成球的形状,一匹不知从何处钻出的骆驼,出现在地平线上。它好奇的打量了一下正在装料的挖掘机,忽然又预感到了什么,掉转头,拼命的向东边跑去。
若羌县的地形很特殊,这是一个在沙海中苦苦挣扎的小城。它的西面是著名的死亡之海--塔克拉玛干沙漠。塔克拉玛干在维语中的意思是进得去、出不来,那里就是死亡的世界、生命的禁区。县城的南面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--库木塔格,每年没完没了的沙尘暴是它最喜欢的恶作剧。北部是平原沙漠区,看着骆驼逃走的方向,东边才是最安全的,这也是动物比人更有预感的证明!
挖掘机的嗡嗡声响此刻在戈壁滩中格外刺耳,一辆辆车子排着队挪动着。忽然,我感觉有一点不对劲,真的,就是一点点。西边,就是我早晨出来的方向,县城的位置。小城突然不见了,代替它的是一座座巍峨高大的山峰。我使劲擦擦了眼睛:没错啊,就是一座山,那么县城哪里去了?
紧接着,对面的山峰开始了移动,慢慢的向我们所在的位置压过来。耳边有了一丝声响,好像谁在窃窃私语,又像是谁在低声的打着口哨,我侧着耳朵,闭上眼睛用力想品出声音的味道。忽然,沙尘暴就来了,还没有等我的眼睛睁开。狂风席卷着沙粒打在了我的脸上,那是一种犹如鞭策的疼痛。工地上,一架堆放柴油、工具的帐篷在暴风中颤抖着、摇曳着。不,那不是摇曳,那是撕扯那是暴虐,在狂风的怒吼声里,帐篷上撕裂的布片“啪啪”作响,它的中间最先破裂,四角固定的长长的铆钉也被揪了出来,在一声绝望的喊声之下,它“嗖”的一下被风暴卷起,消失在莽莽尘埃之中。没有了帐篷的护佑,几只没有油的空桶也跳跃着、翻滚着,叮叮当当的追逐而去。
我挣扎着拉开车门,狂风将我和门一下向前推去,合页发出“吱呀”的断裂声,我差点摔倒,勉强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车门关住。我惊魂未定,揉揉眼角的沙子向车外望去,什么也看不见了,挖掘机不见了,排队的车子不见了,除了灰蒙蒙覆盖在玻璃上的沙子,什么也看不见。除了“呼呼”怒吼的风声和沙粒打在驾驶室上的“啪啪”声,声音的世界一片空白!
经历如此恐怖的沙尘暴,简直魂飞魄散,而常德小胡是付出代价更大。他翻车了,从铁道路基掉了下来……(未完待续)